婚内分居期间继子女抚养费的给付原则及具体处理规则是什么?
作者:未知时间:2025-08-19
婚内分居期间继子女抚养费的给付原则及具体处理规则是什么?
——申某某诉陈某某抚养费案
1.裁判书字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1民终10973号民事裁定书
2.案由:抚养费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申某某
被告(上诉人):陈某某
原告申某某出生于2008年8月27日,其母蔡某与被告陈某某于2012年3月5日登记结婚,并于2012年10月18日生育一子。婚后,原告申某某一直随母亲蔡某与被告陈某某共同生活。自2021年8月起,因感情不和,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与被告正式分居,2021年10月8日被告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被判决驳回。原告认为,被告以长期在外地工作等为由,从2021年8月起拒不承担抚养义务,原告及弟弟由蔡某独自抚养,难以负担抚养费,要求被告支付原告的抚养费。
又查明,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与其生父于2008年8月6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并约定,双方有一预产期为2008年8月27日的孩子(原告申某某),孩子出生后随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共同生活,申某某生父一次性支付蔡某子女抚养费500000元。
另查明,原告申某某现于某学校初中三年级在读,另在外有参加课外补习班等。被告陈某某于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共分十四笔转账给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共计200200元(其中十一笔15000元;10000元、20000元和5200元各一笔)。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现就职于某体育运动公司,年收入约5万元;被告于2018年5月至2021年7月在某酒店担任业主代表,因个人原因于2021年7月6日办理离职手续,2021年工资薪金等收入合计444200余元,2022年度从某实业公司等单位获得的工资薪金等收入合计120800余元,目前无任职受雇信息。
1.原告申某某与被告陈某某之间是否形成了继父女之间的抚养与被抚养关系;
2.被告是否应承担分居期间原告的抚养费。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关于原告申某某与被告陈某某之间是否形成了继父女之间的抚养与被抚养关系的问题。抚养,意为抚育与教养,继父母和继子女关系源于姻亲关系的建立,其“抚养教育关系”的形成既需继子女为未成年人事实外,亦需从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中的照顾及精神上的关爱等方面进行考量。本案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蔡某与被告结婚时,原告年仅3周岁,后即随蔡某及被告共同生活近十年。其间,被告虽因工作原因与家庭成员聚少离多,但也通过承担家庭生活费用、参与家庭旅行等方式,客观上已对原告的生活、教育和成长付出了努力,双方沟通时以父女相称,主观上亦已认可彼此的家庭成员身份。据此,原、被告之间业已形成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
第二,关于被告陈某某是否应承担分居期间原告申某某的抚养费的问题。首先,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不可以随意解除。在形成姻亲关系之初,继父母对继子女的事实抚养主要出于自愿,但构成拟制血亲关系时,已然具备一定的法律意义。换言之,通过抚养教育业已形成的拟制父母子女关系演变成为一种法律义务,其权利义务关系与自然血亲父母子女关系无异,不能自然终止,更不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方解除。同样,考虑到拟制血亲形成的特殊性,可通过双方协议或诉讼方式解除。其次,抚养是独立于赡养之外的法定义务,两者虽然在形式上相互对应,表现为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但并不代表这两者可以对价交换。换言之,父母未尽抚养义务不是免除子女赡养义务的法定条件,免除未来子女赡养义务也不是免除当前抚养义务的法定事由。最后,拟制血亲关系的形成并不影响自然血亲亲子关系的存续,两者可以并存。故,即使原告亲生父亲已提前一次性支付过抚养费,但同时有接受继父母抚养的权利,故被告应根据原告实际需求等因素,承担分居期间合理的抚养费用。
本案中,原告申某某的法定代理人蔡某与被告陈某某的婚姻关系虽仍存续,但存在分居状况,在此期间原告随法定代理人共同生活,被告理应共同承担抚养义务。原告所述的大额支出集中在生活费和课外兴趣班,被告对相应费用和安排的必要性、合理性提出了异议。经查原告现就读初中,尚处在九年义务制教育阶段,应以学校教育为重心,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应结合实际,理性安排,避免加重子女负担和自身经济负担。抚养教育子女系父母的法定职责,父母应根据子女实际需要,结合各自抚养能力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慎重决定,相互沟通、合理安排、统筹兼顾,更应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子女抚养问题。作为被告应通过积极的努力克服暂时的困难,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经济帮助,尽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抚养条件。故,综合原告生父已经支付的抚养费、原告的实际需要、被告的承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定抚养费标准为1000元/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千零七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陈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申某某自2021年8月至2023年4月的抚养费21000元。
宣判后,被告陈某某提起上诉,后在审理过程中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准予上诉人陈某某撤回上诉。
本案系一例继子女追索父母婚内分居期间抚养费的新型纠纷。其争议焦点在于:继父陈某某与未成年继女申某某之间是否形成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以及若已形成,陈某某能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单方行为解除该关系。近年来,随着婚恋观念的更新及家庭形态的多样,重组家庭日益增多,聚焦于继父母子女间拟制血亲关系形成与解除的纠纷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语境下,继父母子女间拟制血亲关系形成与解除条件的认定应采用何种裁判思路、婚内继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标准等问题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仍存在较大争议。
一、未成年继子女权益保护之价值评析
继父母子女关系是一种基于姻亲关系而产生的事实抚养关系,由此可能产生的权利义务包括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以及双方的继承关系。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对此的认定并不等同,本文项下讨论的仅为婚姻家庭编中指向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一)从我国拟制血亲制度的价值转向来看:以“子女本位”为中心
在婚姻家庭编中,继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名分型的纯粹直系姻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双方之间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二是抚养型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双方产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三是收养型的继父母子女关系,适用收养相关规定;四是不完全收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即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是时断时续的,或者有中断的,或者是临时性的。①本案涉及第二种类型,即当继父母对未成年或未独立生活的继子女尽了抚养教育义务时,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形成拟制血亲关系。
从拟制血亲制度的发展来看,各国对其的立法设置有着强烈的传统文化取向。从比较法来看,欧洲多数国家仅仅将父母子女关系界定为姻亲性质,限缩了继父母的抚养责任。例如,《瑞士民法典》规定,将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扶养义务看作配偶之间的协助义务,若是亲生父(母)与继(母)父之间的婚姻关系解除了,那么继母(父)的协助义务也随之解除。②而多数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承认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例如,韩国民法不仅承认前妻之子与后妻之间的继母子关系,也承认历史遗留的正妻与夫之嫡子之间的嫡母子关系,而且认为他们之间是法定的亲母子关系,相互有继承遗产的权利。③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对父母子女关系也从“家族本位”“父母本位”,发展到了“子女本位”,将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发展需要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对比来看,我国立法认可继子女享有拟制血亲及亲生血亲关系的双重法律地位,这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贯彻体现,从价值位阶上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放在了首位。
(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范属性来看:实现家庭稳定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据此认为,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属于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④而现行立法中对于拟制血亲关系的解除,只针对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收养关系的解除作了明确规定,对继父母子女拟制血亲关系能否解除以及解除条件并未规制,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四条有所涉及,认为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时,继父(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母(父)抚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指出,拟制血亲关系可因继父母意思而解除,原则上不能自然解除。据此,在离婚时,明确不同意继续抚养的,可以解除,子女由其生父母抚养。或生父母死亡,在无其他抚养人的情况下,一般不允许解除。①可以看出,无论是判断拟制血亲关系是否成立,抑或是否解除时,均需聚焦于双方关系的稳定性,折射出婚姻家事法保障家庭和谐稳定的功能属性。
综上,在认定“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成立及解除标准之时,始终要坚持我国立法原意,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子女最佳利益及家庭稳定功能实现的双重价值角度进行考量。
二、继父母子女间拟制血亲关系形成条件的认定标准
(一)“具有抚养教育”事实状态的认定应当结合主客观标准
对于抚养关系形成的认定标准,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通说认为,继父母对继子女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要素:第一继父母为继子女给付了经济上的抚养费用;第二,继父母和继子女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第三,继父母对继子女持续抚养教育三年以上;第四,继父母主观上愿意抚养继子女。②实务中,往往结合继父母与未成年继子女共同生活的时间、继父母是否付出必要劳务、是否承担了部分抚育费用、是否有抚养意愿等因素来综合考量。
综上,认定“具有抚养教育”事实状态的成立不宜扩大,需要结合主客观标准,即客观上双方具有稳定的共同生活时间、家庭融合度,且继父母承担了经济上及教育上的抚养职责,主观上双方都不排斥形成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本案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蔡某与被告结婚时,原告年仅3周岁,后即随蔡某及被告共同生活近十年,且被告对原告的生活、教育成本进行了承担,双方之间存在“抚养教育”的事实。
(二)判断“受其抚养教育”关系的形成需侧重考察两个“合意”
相较于亲生血亲子女关系,继父母子女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存在更为复杂的家庭情感及身份认同需求,因此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主动探知当事人主观真意,重点考察是否形成两个合意:一是继父母与生母父间对继子女的合意抚养意愿;二是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对家庭融合度认知。本案中,原告在亲生父母离婚后出生,成长至今从未接触过亲生父亲,与继父被告平时以父女相称。被告与原告母亲婚姻关系稳定期间,经常组织家庭出游、为原告准备生日礼物等,可以说双方主观上趋向形成稳定的父女关系之合意,并且互相认可对方的家庭成员身份。
三、继父母子女间拟制血亲关系解除条件的认定标准
(一)赋予当事人一定条件下的解除拟制血亲的权利
经梳理分析,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类裁判思路:①一是以解除事由发生时继子女是否成年来划分。若已成年,继父母离婚时或死亡时不能自然解除,参照适用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解除收养关系的规定,可以协议解除或诉讼解除②;若离婚时未成年,可自然归于终止③,但也有法院强调此时还需继父母作出解除抚养关系的意思表示,否则不能自然解除①。二是以继承实际发生时为节点确定是否形成抚养关系,认可离婚时,继父母子女关系视为消灭。②三是以当事人主观意愿及客观生活条件为准。解除继父母子女收养关系与否,应当综合考虑双方关系恶化程度、能否共同生活及相关抚养、赡养等实际情况确定。③值得注意的是,在认可婚姻关系自然终止的同时,部分法院仅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成年继子女之间的关系保留了一定协商解除或单方主张解除的空间。
从立法原意可知,在形成姻亲关系之初,继父母对继子女的事实抚养主要出于自愿,仅是道德约束,但构成拟制血亲关系时,其权利义务关系与自然血亲父母子女关系无异。换言之,通过抚养教育业已形成的拟制父母子女关系演变成为一种法律义务,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不可以随意解除。但同时考虑拟制血亲的双重属性,赋予一定条件下的解除权利,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等的有机统一。例如,在离婚继父母明确拒绝的情形下,仍强加抚养义务的话,可能会导致关系恶化下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
(二)宜根据解除事由的发生节点进行类型区分
根据解除事由的发生节点,可将继父母与继子女拟制血亲关系分为四类解除情形:第一,因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第二,再婚关系存续期间,生父(母)死亡;第三,再婚关系存续期间,继父(母)与生母(父)或继父(母)与继子女协商解除;第四,再婚关系存续期间,继父(母)主张拒绝继续抚养继子女。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若离婚时继子女未成年,且离婚时约定或判决由生父母继续抚养,那么“形成抚养教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自然归于终止;若继子女已成年,考虑到抚养义务与赡养义务的权利义务对等性,除双方协商解除或因关系恶化一方主张解除外,一般不予解除。对于第二种情况,若生父(母)死亡时继子女未成年,为保障未成年人抚养状态及成长环境的稳定性,该拟制血亲关系一般不能自然终止,若未成年继子女生(母)父主张由其抚养,可参照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的认定规则进行考察,优先考虑继父母与其生父母抚养能力、生活状态、教育环境、与未成年人情感联系度等考察;若继子女已成年,此情形下认定规则同第一种情形。对于第三种情形,若继子女已成年,且为真实意思表示,则可由双方协商,但不宜通过法律文书进行确认;若继子女未成年,其生父母不能代理其处理身份关系的放弃和解除,要重点考察继子女的实际抚养状态,通过家庭教育引导妥善处理此类纠纷,督导监护人履职,避免造成未成年人无根可依、无亲可育的状态。本案属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解除拟制血亲关系的案件,即第四种情形,人民法院不宜认可当事人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方解除拟制血亲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通过抚养教育业已形成的拟制父母子女关系演变成为一种法律义务,其权利义务关系与自然血亲父母子女关系无异,并且两者可以并存。认可婚姻单方解除权或加剧重组家庭的抚养矛盾,不利于家庭稳定。第二,此情形多发生于其继父(母)与生父(母)感情恶化的阶段,其婚姻状态处于不稳定情形下,可在离婚诉讼或调解过程中一并进行处理。第三,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保障拟制血亲关系的相对安定性,并赋予一定条件下的解除权利,既符合“崇德向善、尊老爱幼”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体现了“和谐”“法治”“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分居期间继子女抚养费的参酌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离婚并非主张抚养费的充分条件,子女可在父母分居期间要求不直接抚养的父母一方支付抚养费。抚养费的数额一般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酌定继子女抚养费支付标准时,除要考量子女实际需要、双方经济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外,还应考虑继子女享有拟制血亲及亲生血亲关系的双重法律地位,在此特殊性基础上,还需考量其生父母的抚养费支付标准,无特别情形下应酌情予以扣除。本案中,考虑到原告正临中考,当前每月实际所需在5000元左右,其亲生父亲曾在十年前一次性支付过50万元的抚养费,结合被告的经济能力水平,最终确定了被告以每月1000元的标准补付分居期间的抚养费。
转载于公众号:甬盈法顾
婚内分居期间继子女抚养费的给付原则及具体处理规则是什么?
——申某某诉陈某某抚养费案
1.裁判书字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1民终10973号民事裁定书
2.案由:抚养费纠纷
3.当事人
原告(被上诉人):申某某
被告(上诉人):陈某某
原告申某某出生于2008年8月27日,其母蔡某与被告陈某某于2012年3月5日登记结婚,并于2012年10月18日生育一子。婚后,原告申某某一直随母亲蔡某与被告陈某某共同生活。自2021年8月起,因感情不和,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与被告正式分居,2021年10月8日被告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被判决驳回。原告认为,被告以长期在外地工作等为由,从2021年8月起拒不承担抚养义务,原告及弟弟由蔡某独自抚养,难以负担抚养费,要求被告支付原告的抚养费。
又查明,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与其生父于2008年8月6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并约定,双方有一预产期为2008年8月27日的孩子(原告申某某),孩子出生后随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共同生活,申某某生父一次性支付蔡某子女抚养费500000元。
另查明,原告申某某现于某学校初中三年级在读,另在外有参加课外补习班等。被告陈某某于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共分十四笔转账给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共计200200元(其中十一笔15000元;10000元、20000元和5200元各一笔)。原告法定代理人蔡某现就职于某体育运动公司,年收入约5万元;被告于2018年5月至2021年7月在某酒店担任业主代表,因个人原因于2021年7月6日办理离职手续,2021年工资薪金等收入合计444200余元,2022年度从某实业公司等单位获得的工资薪金等收入合计120800余元,目前无任职受雇信息。
1.原告申某某与被告陈某某之间是否形成了继父女之间的抚养与被抚养关系;
2.被告是否应承担分居期间原告的抚养费。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关于原告申某某与被告陈某某之间是否形成了继父女之间的抚养与被抚养关系的问题。抚养,意为抚育与教养,继父母和继子女关系源于姻亲关系的建立,其“抚养教育关系”的形成既需继子女为未成年人事实外,亦需从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中的照顾及精神上的关爱等方面进行考量。本案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蔡某与被告结婚时,原告年仅3周岁,后即随蔡某及被告共同生活近十年。其间,被告虽因工作原因与家庭成员聚少离多,但也通过承担家庭生活费用、参与家庭旅行等方式,客观上已对原告的生活、教育和成长付出了努力,双方沟通时以父女相称,主观上亦已认可彼此的家庭成员身份。据此,原、被告之间业已形成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
第二,关于被告陈某某是否应承担分居期间原告申某某的抚养费的问题。首先,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不可以随意解除。在形成姻亲关系之初,继父母对继子女的事实抚养主要出于自愿,但构成拟制血亲关系时,已然具备一定的法律意义。换言之,通过抚养教育业已形成的拟制父母子女关系演变成为一种法律义务,其权利义务关系与自然血亲父母子女关系无异,不能自然终止,更不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方解除。同样,考虑到拟制血亲形成的特殊性,可通过双方协议或诉讼方式解除。其次,抚养是独立于赡养之外的法定义务,两者虽然在形式上相互对应,表现为权利义务的一致性,但并不代表这两者可以对价交换。换言之,父母未尽抚养义务不是免除子女赡养义务的法定条件,免除未来子女赡养义务也不是免除当前抚养义务的法定事由。最后,拟制血亲关系的形成并不影响自然血亲亲子关系的存续,两者可以并存。故,即使原告亲生父亲已提前一次性支付过抚养费,但同时有接受继父母抚养的权利,故被告应根据原告实际需求等因素,承担分居期间合理的抚养费用。
本案中,原告申某某的法定代理人蔡某与被告陈某某的婚姻关系虽仍存续,但存在分居状况,在此期间原告随法定代理人共同生活,被告理应共同承担抚养义务。原告所述的大额支出集中在生活费和课外兴趣班,被告对相应费用和安排的必要性、合理性提出了异议。经查原告现就读初中,尚处在九年义务制教育阶段,应以学校教育为重心,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应结合实际,理性安排,避免加重子女负担和自身经济负担。抚养教育子女系父母的法定职责,父母应根据子女实际需要,结合各自抚养能力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慎重决定,相互沟通、合理安排、统筹兼顾,更应量力而行,妥善处理子女抚养问题。作为被告应通过积极的努力克服暂时的困难,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经济帮助,尽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抚养条件。故,综合原告生父已经支付的抚养费、原告的实际需要、被告的承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定抚养费标准为1000元/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千零七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陈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申某某自2021年8月至2023年4月的抚养费21000元。
宣判后,被告陈某某提起上诉,后在审理过程中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准予上诉人陈某某撤回上诉。
本案系一例继子女追索父母婚内分居期间抚养费的新型纠纷。其争议焦点在于:继父陈某某与未成年继女申某某之间是否形成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以及若已形成,陈某某能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单方行为解除该关系。近年来,随着婚恋观念的更新及家庭形态的多样,重组家庭日益增多,聚焦于继父母子女间拟制血亲关系形成与解除的纠纷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语境下,继父母子女间拟制血亲关系形成与解除条件的认定应采用何种裁判思路、婚内继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标准等问题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仍存在较大争议。
一、未成年继子女权益保护之价值评析
继父母子女关系是一种基于姻亲关系而产生的事实抚养关系,由此可能产生的权利义务包括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以及双方的继承关系。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对此的认定并不等同,本文项下讨论的仅为婚姻家庭编中指向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一)从我国拟制血亲制度的价值转向来看:以“子女本位”为中心
在婚姻家庭编中,继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名分型的纯粹直系姻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双方之间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二是抚养型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双方产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三是收养型的继父母子女关系,适用收养相关规定;四是不完全收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即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是时断时续的,或者有中断的,或者是临时性的。①本案涉及第二种类型,即当继父母对未成年或未独立生活的继子女尽了抚养教育义务时,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形成拟制血亲关系。
从拟制血亲制度的发展来看,各国对其的立法设置有着强烈的传统文化取向。从比较法来看,欧洲多数国家仅仅将父母子女关系界定为姻亲性质,限缩了继父母的抚养责任。例如,《瑞士民法典》规定,将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扶养义务看作配偶之间的协助义务,若是亲生父(母)与继(母)父之间的婚姻关系解除了,那么继母(父)的协助义务也随之解除。②而多数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承认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例如,韩国民法不仅承认前妻之子与后妻之间的继母子关系,也承认历史遗留的正妻与夫之嫡子之间的嫡母子关系,而且认为他们之间是法定的亲母子关系,相互有继承遗产的权利。③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对父母子女关系也从“家族本位”“父母本位”,发展到了“子女本位”,将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发展需要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对比来看,我国立法认可继子女享有拟制血亲及亲生血亲关系的双重法律地位,这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贯彻体现,从价值位阶上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放在了首位。
(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范属性来看:实现家庭稳定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据此认为,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属于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④而现行立法中对于拟制血亲关系的解除,只针对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收养关系的解除作了明确规定,对继父母子女拟制血亲关系能否解除以及解除条件并未规制,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四条有所涉及,认为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时,继父(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母(父)抚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指出,拟制血亲关系可因继父母意思而解除,原则上不能自然解除。据此,在离婚时,明确不同意继续抚养的,可以解除,子女由其生父母抚养。或生父母死亡,在无其他抚养人的情况下,一般不允许解除。①可以看出,无论是判断拟制血亲关系是否成立,抑或是否解除时,均需聚焦于双方关系的稳定性,折射出婚姻家事法保障家庭和谐稳定的功能属性。
综上,在认定“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成立及解除标准之时,始终要坚持我国立法原意,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子女最佳利益及家庭稳定功能实现的双重价值角度进行考量。
二、继父母子女间拟制血亲关系形成条件的认定标准
(一)“具有抚养教育”事实状态的认定应当结合主客观标准
对于抚养关系形成的认定标准,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通说认为,继父母对继子女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要素:第一继父母为继子女给付了经济上的抚养费用;第二,继父母和继子女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第三,继父母对继子女持续抚养教育三年以上;第四,继父母主观上愿意抚养继子女。②实务中,往往结合继父母与未成年继子女共同生活的时间、继父母是否付出必要劳务、是否承担了部分抚育费用、是否有抚养意愿等因素来综合考量。
综上,认定“具有抚养教育”事实状态的成立不宜扩大,需要结合主客观标准,即客观上双方具有稳定的共同生活时间、家庭融合度,且继父母承担了经济上及教育上的抚养职责,主观上双方都不排斥形成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本案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蔡某与被告结婚时,原告年仅3周岁,后即随蔡某及被告共同生活近十年,且被告对原告的生活、教育成本进行了承担,双方之间存在“抚养教育”的事实。
(二)判断“受其抚养教育”关系的形成需侧重考察两个“合意”
相较于亲生血亲子女关系,继父母子女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存在更为复杂的家庭情感及身份认同需求,因此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主动探知当事人主观真意,重点考察是否形成两个合意:一是继父母与生母父间对继子女的合意抚养意愿;二是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对家庭融合度认知。本案中,原告在亲生父母离婚后出生,成长至今从未接触过亲生父亲,与继父被告平时以父女相称。被告与原告母亲婚姻关系稳定期间,经常组织家庭出游、为原告准备生日礼物等,可以说双方主观上趋向形成稳定的父女关系之合意,并且互相认可对方的家庭成员身份。
三、继父母子女间拟制血亲关系解除条件的认定标准
(一)赋予当事人一定条件下的解除拟制血亲的权利
经梳理分析,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类裁判思路:①一是以解除事由发生时继子女是否成年来划分。若已成年,继父母离婚时或死亡时不能自然解除,参照适用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解除收养关系的规定,可以协议解除或诉讼解除②;若离婚时未成年,可自然归于终止③,但也有法院强调此时还需继父母作出解除抚养关系的意思表示,否则不能自然解除①。二是以继承实际发生时为节点确定是否形成抚养关系,认可离婚时,继父母子女关系视为消灭。②三是以当事人主观意愿及客观生活条件为准。解除继父母子女收养关系与否,应当综合考虑双方关系恶化程度、能否共同生活及相关抚养、赡养等实际情况确定。③值得注意的是,在认可婚姻关系自然终止的同时,部分法院仅为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成年继子女之间的关系保留了一定协商解除或单方主张解除的空间。
从立法原意可知,在形成姻亲关系之初,继父母对继子女的事实抚养主要出于自愿,仅是道德约束,但构成拟制血亲关系时,其权利义务关系与自然血亲父母子女关系无异。换言之,通过抚养教育业已形成的拟制父母子女关系演变成为一种法律义务,具有抚养教育的继父女关系不可以随意解除。但同时考虑拟制血亲的双重属性,赋予一定条件下的解除权利,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等的有机统一。例如,在离婚继父母明确拒绝的情形下,仍强加抚养义务的话,可能会导致关系恶化下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
(二)宜根据解除事由的发生节点进行类型区分
根据解除事由的发生节点,可将继父母与继子女拟制血亲关系分为四类解除情形:第一,因继父(母)与生母(父)离婚;第二,再婚关系存续期间,生父(母)死亡;第三,再婚关系存续期间,继父(母)与生母(父)或继父(母)与继子女协商解除;第四,再婚关系存续期间,继父(母)主张拒绝继续抚养继子女。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若离婚时继子女未成年,且离婚时约定或判决由生父母继续抚养,那么“形成抚养教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自然归于终止;若继子女已成年,考虑到抚养义务与赡养义务的权利义务对等性,除双方协商解除或因关系恶化一方主张解除外,一般不予解除。对于第二种情况,若生父(母)死亡时继子女未成年,为保障未成年人抚养状态及成长环境的稳定性,该拟制血亲关系一般不能自然终止,若未成年继子女生(母)父主张由其抚养,可参照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的认定规则进行考察,优先考虑继父母与其生父母抚养能力、生活状态、教育环境、与未成年人情感联系度等考察;若继子女已成年,此情形下认定规则同第一种情形。对于第三种情形,若继子女已成年,且为真实意思表示,则可由双方协商,但不宜通过法律文书进行确认;若继子女未成年,其生父母不能代理其处理身份关系的放弃和解除,要重点考察继子女的实际抚养状态,通过家庭教育引导妥善处理此类纠纷,督导监护人履职,避免造成未成年人无根可依、无亲可育的状态。本案属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解除拟制血亲关系的案件,即第四种情形,人民法院不宜认可当事人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方解除拟制血亲关系。理由如下:第一,通过抚养教育业已形成的拟制父母子女关系演变成为一种法律义务,其权利义务关系与自然血亲父母子女关系无异,并且两者可以并存。认可婚姻单方解除权或加剧重组家庭的抚养矛盾,不利于家庭稳定。第二,此情形多发生于其继父(母)与生父(母)感情恶化的阶段,其婚姻状态处于不稳定情形下,可在离婚诉讼或调解过程中一并进行处理。第三,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保障拟制血亲关系的相对安定性,并赋予一定条件下的解除权利,既符合“崇德向善、尊老爱幼”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体现了“和谐”“法治”“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分居期间继子女抚养费的参酌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离婚并非主张抚养费的充分条件,子女可在父母分居期间要求不直接抚养的父母一方支付抚养费。抚养费的数额一般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酌定继子女抚养费支付标准时,除要考量子女实际需要、双方经济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外,还应考虑继子女享有拟制血亲及亲生血亲关系的双重法律地位,在此特殊性基础上,还需考量其生父母的抚养费支付标准,无特别情形下应酌情予以扣除。本案中,考虑到原告正临中考,当前每月实际所需在5000元左右,其亲生父亲曾在十年前一次性支付过50万元的抚养费,结合被告的经济能力水平,最终确定了被告以每月1000元的标准补付分居期间的抚养费。
转载于公众号:甬盈法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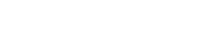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31010702006146
沪公网安备31010702006146

